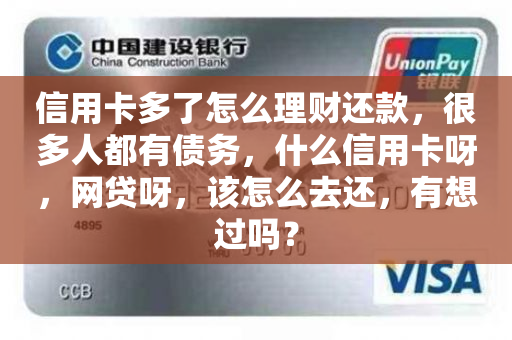才能把亲情或人心看透彻你认同这句话吗
才能把亲情或人心看透彻你认同这句话吗?
一九五七年,在我那封建意识浓厚,古板又固执的小脚金家掌门人一一我的老神仙祖母逝世后的笫五年,金家吩星星吩月亮的传宗结代的独儿子一一我的唯一的弟弟降临在金家,那时我母亲己近三十八岁属高龄产妇,在上世纪那个年代己实属福大命大,更危險的是在自己家中临盆产子,风險几高哟,接生的是我后街的一个传统接生婆,那时的人还没有风險意识,六个糖水鸡蛋四把挂面,接生费几元就给姜孃孃(接生婆)壮了胆,连拉帶扯又加上我母亲配合,在全家人揪心骇胆又满怀期望中,我弟第一出娘胎就迫不接待的拉了一泡血屎,接生婆一看就像算卦的先生一样告诫母亲,老江,你这个儿以后可能是个混世魔王不大好管,你不要掼势哟,不然,给你惹祸的日子在后头,千切记住,说完吃了该吃的,拿了该拿的,喜滋滋走了,替送子娘娘完成了一项任务,功德又圆滿了一次。我父母沉浸在喜悦中,接生婆的语哪还放心上,焚香告慰祖宗,金家有香炉钵钵了,天上几个老神仙祖宗可以闭眼了,老封建祖母的铜烟杆不必甩了,袁大头不必吹和听了,要在的话铁定喊赏,但到底赏哪个我就无从知道了,反正不是我。弟第一出生,我就成了背夫,从一岁到五六岁,基本上都是在熊爹爹和我背上长大的,因是独儿,父母溺爱至极,他是儿王,我是听用,什么都紧他,渐渐养成了又自私又专横调皮到顶的一个小波皮,真应了接生婆预言,我七岁一一十二三岁那些年吃尽了他的苦头还不敢说,我母亲的原则你是长姐就应迁就他替父母分忧,只有熊爹爹知道我的委曲,但那又能怎样,他老人家只有用那汗浸浸的胸膛替我挡风挡雨挡指责,别无他法,随着光阴曰月梭过到了八零年,我弟弟内安排进了父单位,干了两年,停薪留职和他朋友去云南文山种花椒树,资金各出一半,我当时家庭变故夫君早逝,抚恤金加工作时存的二千元钱放在母亲那里被他全部拿走加上父母给的,屁股一拍到了文山当了椒农,他一个公子哥儿当得了什么创业户哟,三年下来,经管不善血夲无归,他那朋友看情况不对马上撒退,把创业户一人扔在了麻栗坡,当吋他们在麻粟坡和越男人接洽,结果我弟成了欠債主孤家寡人脱不了爪爪,我父母急得三魂掉了二魂,我俩儿女在娘家又抽不出身,只好电报当吋在兴义的我,要我想办法凑一万元救急,对方是回族,不好惹,不然小命难保,没办法,亲情于天,我不帮无人帮,只好把自己的积蓄在向朋友处暂借告急,我火烧火燎的赶到文山,交钱续人,一看,我的天,这哪是我一母同胞的弟哟,分明就是个越男人,又黑又瘦,如穿上黑衣,拖双凉鞋,头代尖斗草鞋,说他是标准越男人无疑,这是后话了,光阴又到了零一年,我父亲仙逝,不知我弟在何方,八七年我母亲被陕西过境串闯死,我弟不知在何方,俗话说,亲欲在子不远游,但我双亲逝世,他们的儿子就像世问蒸发了一样,你又能怎样,他们的女儿充当了孝子,奉送了双亲,你总不能登广告普天下寻他吧,光阴又梭到了一六年,金家香炉钵钵回来了,这些年无音迅,出玩在我面前,他不喊我长姐我己认不识他了,两姐弟相聚才知这二十多年在西安发展,总算浪子回头,属金不换了,经历了几十年的江湖沉浮,岁月磋砣,脸上己布滿了瘡桑,我这几十年我己不想问,他也不想说,一切尽在不言中,临走留下十万元,说补偿我,当初没有长姐两肋插刀,就没有他的今天,钱虽不多也是一片心意,双亲没尽孝,长姐如母,就这样了,我泪眼望着他,一个当年的混球被岁月这把挫刀挫成了一块铁皮,也是命里斯,运里斯了,临分别吋,我把钱还给他,叫他好自为之,心中有姐常牵挂,毕竞一母同胞,血浓于水,游子远游,家乡才是根,才是永远的窝,最后,我弟给我跪下,一定要我替代父母亲受他一跪,谢罪父母仙逝他不孝的陪罪。唉,醒误晚矣,父母在,子不远游,这是祖宗们留下的一可忠言,你不信是不行的。